回歸以來最大的轉變,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進退演化,並由此浮現出四大矛盾和轉機。
回歸二十年,基於香港特殊的歷史,以及中央給予的「五十年不變」政治承諾,人們往往以「變與不變」作為主要觀察點。不過,在歷史長河中,二十年只是一個小節點,大家要放眼前看,要認真總結香港在「一國」和「兩制」獨特雙重優勢下的實踐經驗,疏理期間浮現的矛盾和轉機,以便砥礪前行、煥發新機,為香港謀劃更大的發展,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曾是中華民族因腐敗晚清而遭逢西方強權欺凌的屈辱印記,也是國家改革開放躍升繁榮豐盛的點火石。百餘年來,作為中西新舊交匯的文化碰撞點,香港發展出兼收並蓄、思想奔騰、只談經濟、迴避政爭的特有氣質。
九七回歸前夕,政治變化於香港人心中醞釀的複雜情感,促成另一波移民潮,被海外媒體解讀為所謂「香港大限」的註腳,但同時亦有更大量的港人回流,讓「香港已死」之類的悲觀論調成為笑柄。
從港英到特區,一國兩制的落實,基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需要中央、特區政府及港人之間互信互容,以及相互探索、衝撞、調適。這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期間經歷了不少轉變折騰,中央始終秉持對港的關顧扶持,也多有挹注,讓香港屢經金融危機而不墜,司法獨立原則亦獲保存;對於特首選舉的安排更是費煞思量,在堅持一國底線之上,盡量提供「寬鬆」的空間。
然而,期間亦面對不少內外危機和困境,更出現不少合理或誤導性的質疑和批評,特別是因與國際脈動高度連結,持續受到所謂世界潮流和國際力量的牽引和連動,在政治和社會發展方面,愈益刻意要求展現有別於過往、有別於「一國」的「香港模式」,甚至不惜以「兩制」去抗衡「一國」,不惜以癱瘓經濟去實現這種政治目的。特區在回歸後持續顛簸跌宕,正是肇因於此。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回歸二十年的最大的轉變,就是香港與中國內地、特區與中央之間的進退演化,並且由此浮現出四大矛盾和轉機。
第一,從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去挑戰中央的主權地位。其中,行政長官作為特區之首並向中央負責,由其掌領的行政主導體制,以及中央對特首和問責團隊的實質任命權,這是基本法所訂定的權力,但卻一直受到香港泛民主派的質疑和批評,並被認定為一國兩制和特區高度自治是否受「干預」的指標。
其次,立法會作為特區的立法機關,所有涉及特區事務都在其立法範圍內,中央不會干預,但具備領導地位和職責。立法會無論是其議員選舉、言行政綱、就職宣誓、立法提案、辯論話題、會議規則等,一旦觸犯國家主權,違悖國家法規時,特區政府或特區法院都應依法及時處置,而若中央直接依法介入,也不屬違反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原則。但這種情況卻是屢禁難停,似在挑戰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底線。
再者,假借訴訟和司法覆核,反對派假借特區司法挑戰中央主權的做法,將香港的前途交由法院作終極裁決,自回歸至今便一直存在,會否令行政主導體制受顛覆,情況需予關注。
第二,本是額外授權的高度自治被膨脹為尚方寶劍。在基本法下的「兩制」或高度自治權力,本就是中央對香港的額外授權,並沒有所謂的剩餘權力,但有人卻反客為主地指:「除了國防外交,甚麼都是香港的。」涉及國家主權的主從關係,必須要實事求是,準確和全面認識香港政治體制設計,以及中央和香港關係並要理解其背後因由,從不理會誰的聲音大,香港還憑甚麼硬拗呢?
第三,教育缺失「製造」國家認同問題。這個問題源於英國管治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洗足十代人的腦」,而「九七世代」則因中史和國民教育的疏失而從無國民身份感覺,談不上身份認同;相反,在面對個人成長和向上流機會少的壓力下,將個人怨憤倒傾在身份認同方面,這是尋求代罪羔羊的心態扭曲。
第四,回歸以來的經濟表現顯然大不如前,但是仍能保持基本繁榮,實質總體GDP二十年內增長近百分之八十八,失業率低企,外匯儲備豐足,從此等意義上來看,資本主義香港的「一國兩制」落實得尚算成功,經濟自由也保持得不錯,在世界的各種排名之中,香港的經濟自由與競爭力一直都名列前茅。不過,香港的經濟理應是可以有更佳表現的,但就是不與內共融,即使中央給予「大堂前座」優勢,但不領情就是不領情,結果是自我被邊緣化。今天,中央再給予「一帶一路」、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接受與不接受,唯憑大家的一念之間。
原本轉載自《亞洲週刊》2017年7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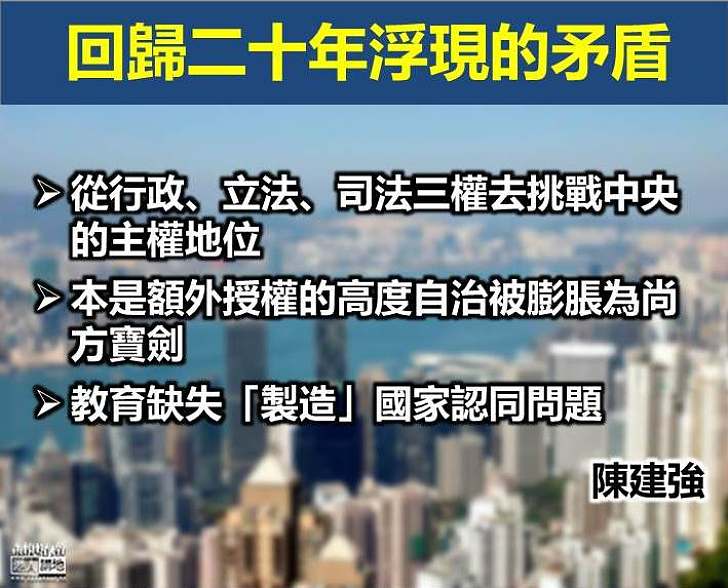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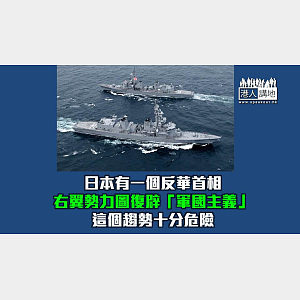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