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惻隱之心——孟子以孺子快將墮井為例,說明人人皆有惻隱之心。當我們見到孺子快墮井時,自然就會有焦急與痛惜之心,不是源於任何利益關係的考慮,如與孺子父母的交情、博得鄰人的稱讚、討厭獲得麻木不仁的名聲。孟子認為這種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仁之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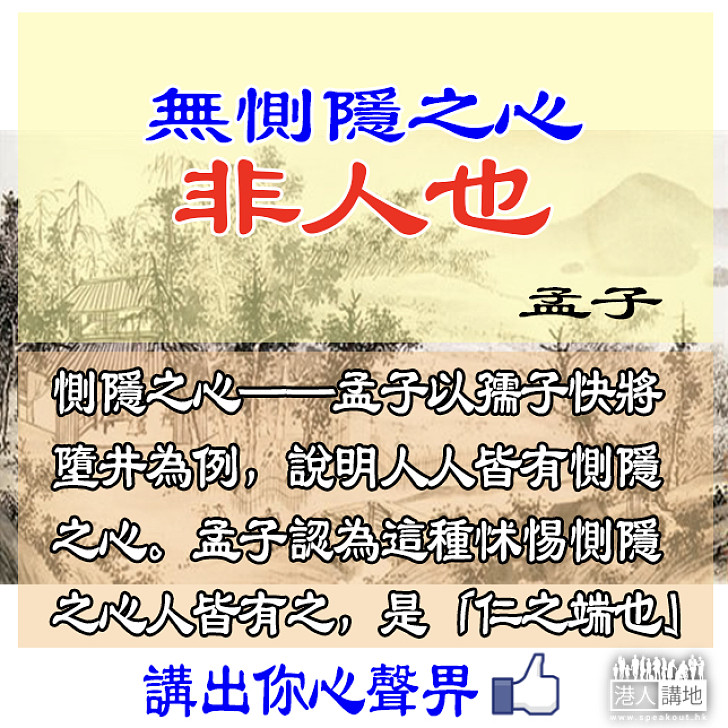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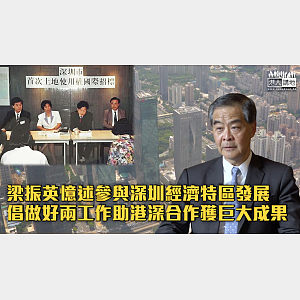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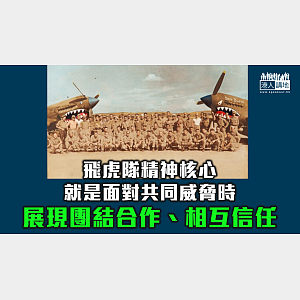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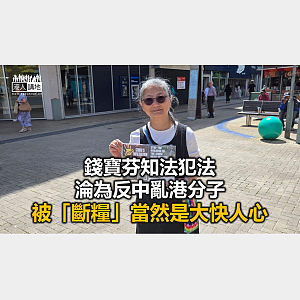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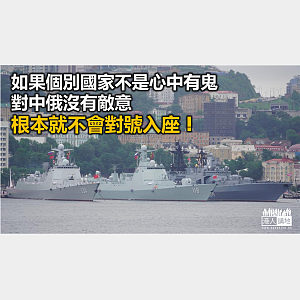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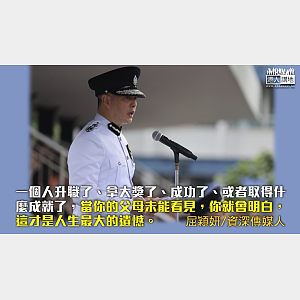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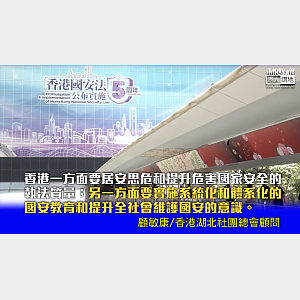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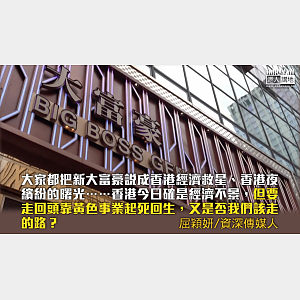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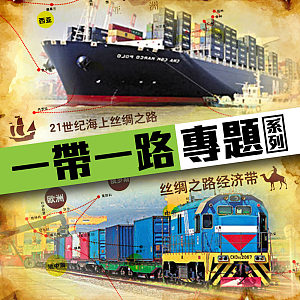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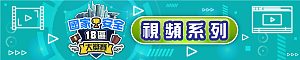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