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央政策組顧問、中大社工系教授 王卓祺
最近,無電視節目《新聞透視》有一個兩集的特輯回顧《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三十周年,其中一集專題講述已於1994年解散的政治團體「匯點」的幾位朋友,回顧他們「民主回歸」的心路歷程,筆者是其中之一。匯點是我與一班大學友好在1983年1月正式成立的。
另外一件事是最近同時發生的,就是老朋友、好朋友曾澍基教授逝世。我與他一起有份成立匯點,並一起與劉迺強三人於1993 年1 月脫離我們一手創立的組織。由於曾澍基離世,亦引起一些人討論「民主回歸」是否已經曲終人散的問題。再者,香港圍繞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爭論,中央政府「落閘」,嚴格規定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以至有人認為港人民主、高度自治此路不通,並以此論證民主回歸路線失敗。基於這三點,勾起了筆者對民主回歸路線實踐三十年的反思。本文首先論證民主化與民主回歸的問題,並論及香港政制改革的障礙所在;繼而評論民主回歸是歷史的選擇,民主反共路線是自絕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洪流。
民主化與民主回歸
民主是一個過程,即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因此才有學者用民主化形容非民主政體國家過渡至民主政體的過程。例如美國1776年立國至1965年,即一百八十九年後絕大部分黑人才實際上有選舉權,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又例如亞洲的泰國,最近軍人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而當權,這是回潮。簡單一點的解釋是,政治制度的產生及變化是社會力量鬥爭及文化價值取捨的綜合結果。不要幻想有一個適合任何時空背景的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們的選擇不是最優的理想化制度,而是適合本身情況的政體,若我們非要事事最理想化,到頭來是一事無成。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大家贏一些,輸一些,可能才變成現實。
香港的民主化便是一個一點一滴累積的過程,關鍵點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設計有信心,不允許把權力落入反共人士手中。香港政制發展的問題就是這樣簡單,但亦由於一些人不能接受這一個限制而障礙重重。以下是我理解香港民主化過程點滴累積的幾個重要里程碑:
.1982 年開始有選舉產生的區議會議員;
.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
.1991年立法局首次引入直選議席;
.由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英未能就「直通車」,即英治立法局議員過渡至特區立法會議員,導致中方自行成立臨時立法會;
.1997 年第一任特首由4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2005年,泛民主派否決2007年特首及2008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香港政制原地踏步;
.2010 年民主黨與中央政府達成協議,立法會通過特首選舉委員會擴大至1200人,立法會擴大至70席;
.2014年6月10日中央政府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突出主權、國家安全高於繁榮安定的取態,預示8月底宣布2017年特首選舉「落閘」,嚴格篩選候選人的規定。
若有人說這個民主化進程不是民主,那麼,請他告訴我什麼是民主?問題應該是,香港的民主進程並不符合一些人的期望而已,致有偏執地認為民主回歸已經失敗,而沒有客觀的論證。
為什麼有些人不顧客觀事實,而歇斯底里否認民主回歸的事實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亦想引用筆者與曾澍基2004年4月17日在《信報》聯名撰寫的文章《後釋法時期的觀念轉變》。當年我們這樣寫的:「釋法標誌香港實質進入『一國兩制』,首六年中央政府對董建華領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信任,所以採取『善意放任』或『善意不介入』的政策;釋法是中央政府首次主動介入特區政治事務……釋法標誌香港政治生態已經有實質改變。香港政黨及民間爭取普選的團體的對手並不純粹是特首董建華,主要還有中央政府。」
十年前的文章繼續這樣寫:「為何中央政府要一改她六年來『善意放任』的對港政策呢?……她的憂慮,例如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會否選出有外國關係及敵視中央政府的人士?對於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程序公平的人來說,這是較難理解的,我們只眼於選舉的公平性、認受性,而沒有考慮如何把『一國』的觀念體現在選舉設計之中,使中央放心。」
看來,我們這一代人一點長進都沒有;三十年來都是反覆圍同一個問題轉。
自絕於歷史的民主反共路線1984 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其中並無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的條款。1990 年頌布的《基本法》卻出現了行政長官「可以選舉或協商產生」的第45條。這說明什麼?就是八十年代筆者等當時的年輕人,已經成功爭取落實民主回歸,而最大的民主回歸派除了當年的匯點之外,還有誰?若我們對歷史負責任的話,答案是中央政府。大家不要忘記,《基本法》出台是1989年六四之後,中央政府仍然有信心把普選的選擇寫在《基本法》內,這一點並不簡單。現在爭取普選的一些語無倫次的人還說,中共過橋抽板,是走數。
近日香港出現的激進運動,當然有它的社會基礎,但是也有它的意識形態性——就是反共,甚至反華!它的社會性體現在曾澍基所言香港回歸中國大陸的「不對稱融合」。筆者亦就此,在《明報》寫了篇文章《香港大勢已去嗎?香港內地的不對稱融合》。依照這個思路,香港目前的政治流派的分類可以融合及對抗融合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不言而喻,這指標是對應十三億人口、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而她可以在短短的三十年,由一個一窮二白的經濟落後國家,變成今天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她的一舉一動已經深深影響與她有來往接觸的國家及地區。
在社會層次,香港與內地的不對稱融合產生心理不平衡——香港人從以前下視內地同胞為「阿燦」,變成今天自嘲為「港燦」。當這心理不平衡,再結合意識形態的敵意,結果亦清楚不過,就產生可以理解的「弱者」自保,拒絕融合的狹隘本土城邦論以至港獨情緒。港獨是新生事物,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界定它為癬疥之疾,不可能有前途的。
不過,港獨之外還有香港始於七十年代、我們這一輩學運社運走過來的民主派分支,稱為泛民主派的民主反共派。這一流派亦沒有前途,除非中國共產黨短中期內會因內部貪腐、一黨專政而倒台。不過,筆者見到的是一個有能力為中華民族一掃近百年恥辱的政治力量,她愈來愈像披馬克思主義外衣,實踐中國傳統中央集權,依靠有自我改造能力的龐大、但基本上還是以業績為主的執政官僚集團。這是實踐儒家的民本主義。
尋回隔絕的歷史
如果一個有能力為民族洗刷恥辱的執政集團,她又把中國的世界地位逐漸回復應有的位置,人民生活又真的有實質改善,就算是掌權者分多一點,民眾會否由於西方宣傳的最理想民主政體而進行另一次革命嗎?這樣一個中華民族復興勢頭,誰可阻擋呢?你若能客觀評估,香港的民主反共派有希望嗎?長期而言,中國朝代更替亦平常事,若將來的中共執政者未能回應歷史需要、人民的期望,她倒台是必然的。
有位久未見面的朋友,兩年前寫下一篇短文《逝去的社會派》,文中感慨當年鼓吹民主回歸的社會派(指匯點,而七十年代學運稱為社會派),當它「面對的是一個隔絕了歷史的社會,當它必須提出『民主回歸』口號時,也就是無可避免要面對歷史了……對歷史的不同理解就終於導致灰飛煙滅的結果」。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盧荻教授這一番說話,其實最適用於這樣一個拒絕在一國框架下實踐民主的民主反共派。盧荻觀察社會派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行動專注於眼前切實可做的」。我和曾澍基的說法是,接受次優選擇——「香港的理想選舉制度設計並不是以『最優』為選擇,而是『次優』的選擇。因為要平衡『一國』及『兩制』的矛盾,我們就要放棄部分執」。
當然,一些香港人不願意尋回隔絕的歷史,我亦無可奈何,他們有人身及思想自由!但是對於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民主回歸是最好的、客觀可行的次優選擇!
原文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4年9月30日
原圖:www.dscn.inf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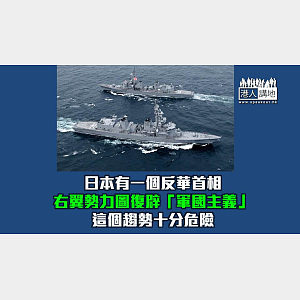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