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哥華逛了數天之後,是時候到卑詩省首府Victoria探望久別了的友人。臨行前先交待入住的酒店名稱和位置,久居香港的美籍友人戲言: 「噢,你何時變得那麼殖民的呢! 」
從列治文南部的Tsawwassen碼頭登船,沿海景色,盡入眼簾,吃過午飯後,不消兩小時,已到達Victoria的Swartz Bay,轉乘巴士往市中心,沿途盡是牧場與農莊,典型北美小鎮的風貌,與市中心的英式維多利亞建築,大相逕庭。
到酒店登記過後,大堂經理推薦酒店有名的英式印度咖哩自助餐,起初摸不著頭腦,但想到印度曾為英國殖民擴張的樞紐,又或許是為遊客精心打造的殖民景觀,販賣歷史聯想而已。友人不甚嗜辣,故亦不了了之。
路上大多是紀念品店、時裝店、餐廳、酒吧等等,偶有數間新舊書店,遊客亦絡繹不絕。友人問道: 「你可覺得Victoria殖民色彩十分濃厚? 」起初還以為他在取笑著我入住的酒店,我說: 「算了罷,加拿大還不是奉行多元文化及種族政策的嗎? 」友人冷說: 「你跟我來,帶你看點東西。」不消一會,已踏進卑詩省的國會大樓,天井引入柔和的自然光,投射在一首原住民手製的木伐上,令遊人不得不注目觀看。大樓外的維多利亞女皇雕塑,是權力的象徵,與大樓遙相呼應,而安放在雕塑左側的,正是一支原住民的圖騰柱。坦白說,是有點格格不入的,尤其明白原住民在美洲殖民歷史上被大舉獵殺與驅逐時,這根圖騰柱,與英式印度咖哩,是否展示著殖民者的仁愛寬厚。淡化了的血腥與悲痛,總會令人好過一點,甚至更容易忘記。
展示是記憶的軌跡,也是權力的伸延,反正展示甚麼,應牢記甚麼,從古至今,從來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決定。眼前的圖騰柱,是紀念品店的商品,是三文魚禮盒上的包裝,與英式印度咖哩,一同充塞著遊人的歷史聯想。不其然想起在維多利亞港浮動著的紅色中式漁船,想起示威者手上的港英殖民政府龍獅旗,與Victoria的英式印度咖哩與圖騰柱,是否同出一轍? 在浪漫化香港殖民過去,那充斥著血與淚的回憶,又應否隨便抹去?
圖:cnc.wallc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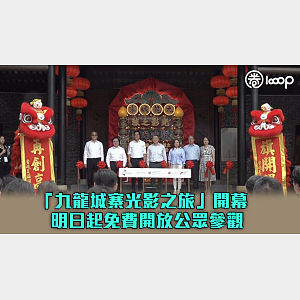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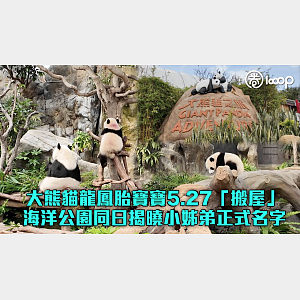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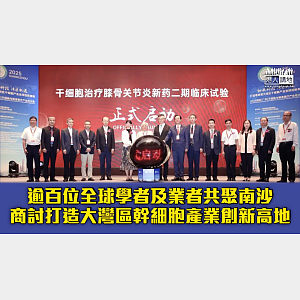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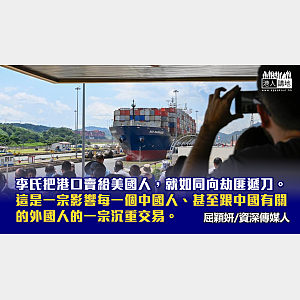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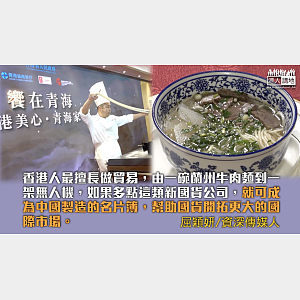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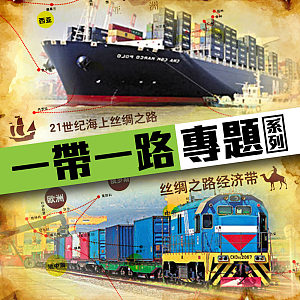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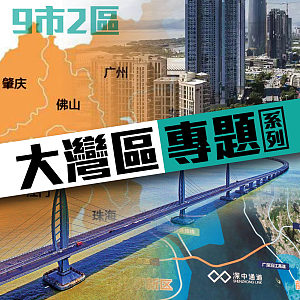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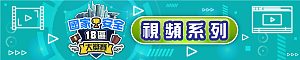




評論